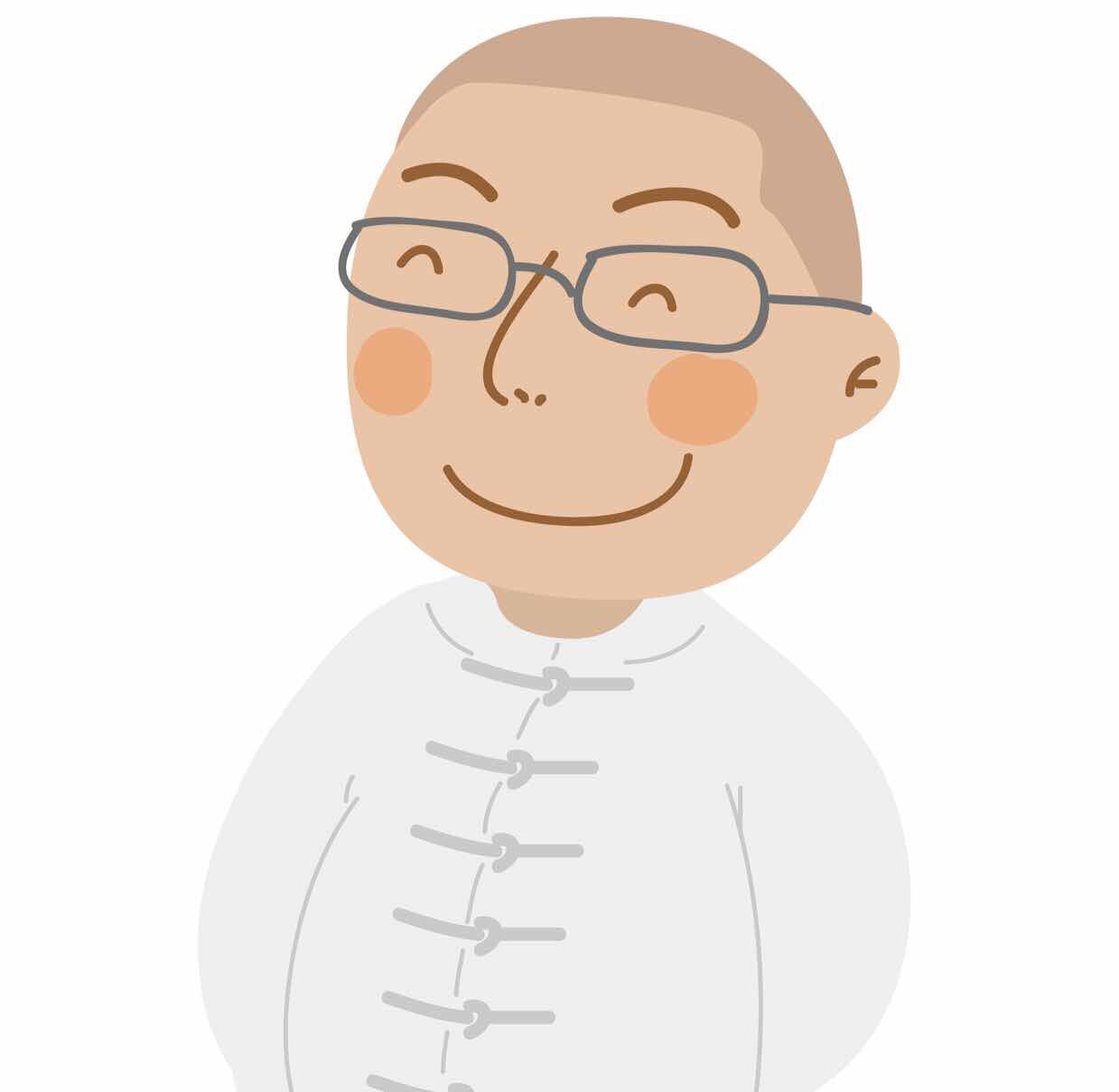休谟与奥威尔谈写作
坏文风
今年与友人讨论学术话题时,抄送了一篇文献的核心假设,如下:
假设1 因此,如果所有事情都同样(为了简化,这里忽略了自我归类的人类水平)的话,在自我归类个人水平的显著性和社会水平的显著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反向的关系。社会自我知觉(social self-perception)往往是沿着一条连续体——从把自我知觉为一个唯一的人(把个人内部的认同最大化,同时把知觉到的自我与其他内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最大化)到把自我知觉为一个内群体类别(把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最大化,同时把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最大化)——而变化。
在这一连续体的中间(在这一点上,自我知觉保持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个体往往认为把他或她自己与内群体成员具有适度的不同;接着,内群体成员又会被看成与外群体成员具有适度的不同。因而,个人的自我归类与内群体-外群体归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在大多数时间里,它们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不过它们的知觉效应却是反向关联的。
因此,按照罗施(Rosch,1978)的观点,社会自我知觉的“基本水平”——也就是往往把类别内的相似性,进而把类别之间的差异性最大化的抽象水平——并不是不变的,而是由个人的自我-内群体差异与内群体-外群体差异之间的反向关系来确定的一个可变物。在任何特定时刻,在个人、内群体及外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是变化的,因此适当的抽象(这种抽象会使认知的简化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最大化)水平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还会保持不变的是,为了减少群内相似性(intragroup similarity)和群际差异性(intergroup difference)的知觉,人们往往会产生个体内相似性(intra-personal similarity)和人际差异性(interpersonal difference)的认知倾向;反之亦然。
假设2 提高内群体-外群体归类显著性的因素往往增加了在自我与内群体成员之间知觉到的的一致性(相似性、等价性、可交换性);同时也增加了知觉到的不同于外群体成员的差异性。因而,这会使刻板化维度——这一维度界定了相关的内群体成员身份——上的个体自我知觉去个性化(depersonalize individual self-perception)。去个性化是指“自我刻板化”(self-stereotyp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某个社会类别中可交换的范例,而不是由他们不同于他人的个体差异所确定的独特个人。
假设3 自我知觉的去个性化是决定群体现象(社会刻板印象、群体凝聚力、种族中心主义、合作和利他主义、情绪感染和移情、集体行动、共同的规范和社会影响过程等等)的基本过程。
最后这一假设概括了整个理论的要点:这一观点假定,在代表了自我知觉的去个性化的方向上,群体行为表示了人们在自我归类的抽象层次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把自我看成是某个社会类别中可交换的范例,而不是由不同于他人的个体差异所确定的独特个人。
然而,去个性化并不是失去个人的特性,也不是失去自我或把自我淹没在群体之中[像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这一概念一样],更不是回归到更原始或无意识的认同形式当中去。它是从个人水平的认同到社会水平的认同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自我概念的性质和内容上的转变,以在更包容的抽象水平上符合自我知觉的功能。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把去个性化看成是认同的获得,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可以按照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它们是由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来行动。在以下各节,我们将简要讨论去个性化的前提和某些后果。
每个字,她都认识,连在一起,不认识了。这样的文字,在心理学文献中比比皆是。
好了,将这样的文字扔到一边,来看看,好的文风是什么。
休谟:谈谈随笔
人类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过一种单纯的动物式的生活,而致力于心灵的种种活动;这些人可以区分为学者和爱交际的两种类型。
学者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所选择的是从事比较高级和困难的心智活动,需要许多闲暇时间来从事单纯的个人思考,要是没有长期的准备和严格的劳作,就不能完成这种工作。社交界则是由喜欢交际的人的种种兴趣爱好汇聚而成:愉快的鉴赏,轻松优雅的理智,对各种人类生活事务明白的思考,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对具体事物的缺陷或完美的观察,把这些人们聚集在一起,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光凭个人孤寂地进行是不行的,需要有同伴,需要与同类的人交流谈话,以获得心智上应有的训练。这样做能使人们结合成为社会团体,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以他力所能及的最好方式发挥他对种种问题的见解,交流信息,彼此得到愉快。
学者与社交界脱离,似乎是上个世纪的一大缺陷。这对于学者的著述活动和对社交界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因为,要是不借助于历史、诗歌、政论和哲学中种种明白的道理,还会有什么交谈的题目能适合于有理性的人的需要呢?那样,我们的全部交谈岂不都成了无聊乏味的唠唠叨叨了吗?那样,我们的心智还能有什么增益,除了老是那一套:
- 没完没了的胡吹瞎说、琐屑之谈;
- 张家长,李家短;
- 搞得糊里糊涂,意乱心烦。
这样消磨时间,在同伴间是最不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生活中最无益的事情。
另一方面,学者的活动由于关闭在学院的小房间里与世隔绝,缺乏很好的交流与伙伴,也同样受到很大的损害。由此产生的恶果是,我们称作belles lettres①(文采)的一切都变成为生硬艰涩的文字,毫无生活和风度上的情趣,也毫无思想和表述上的流畅机智,这些只能从人们交谈中才能得来。甚至哲学也会由于这种沉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受到严重损害,要是它的陈述方式和风格使人感到莫明其妙,它的论断就会成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确实.如果人在推理时一点也不向经验请教,一点也不研究经验(这些经验唯有在公共生活和交谈里才能得到),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些别的什么呢?
我高兴地看到,本世纪的文人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种使他们同人们保持距离的羞答腼腆脾气,同时世人也从各种书籍和学间里得到他们最适当的交谈主题。可以期望学者和社交界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愉快的联盟,会进一步增进彼此的收益;就这个目的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我努力奉献给公众的那些随笔更为有益的了。从这个考虑出发,我认为自己颇像从学者的国度迁居到社交界“国家”的侨民或是派出的使者,我的职责就是促进这两个有重要依存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我要把社交界活动的消息报道给学术界,并且可以把我在自己“国家”里发现的适于社交界“国家”需要的那些商品,输人到这个“国家”。对于贸易平衡问题我们无需担心,保持这种双方的平衡也没有什么困难。在这种商品交换中,原材料主要是由社交界和公共生活领域提供的,而加工产品的工作,则属于学者。
一名大使如果不尊重他出使国家的君主,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玩忽职守的错误;同样,我若是对于社交界的女性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尊重,也是不可宽有的,因为她们是社交王国的女王。我在接近她们时一定要非常尊敬,不能像我本国人那样的作风。学者是人类中最坚持独立性的人,他们极端珍视自由,不习惯于顺从,而我则应当对文雅公众的这些有权威的女王表示顺从。做到这一点以后,我的进一步使命无非就是去建立某种攻守联盟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即反对理性和美的敌人,亦即愚钝的头脑和冷酷的心肠。从这时起我们就可以用最严格猛烈的火力来追击这些敌人,不要宽恕它们。我们的宽容只适用于健全理智和美好情感这类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这类品质总是不可分离地存在在一起的。
抛开上面的比方,认真地说,我以为有理智和教养的妇女们(我只对她们表示敬意)对于各种文艺作品的品评能力,比同等水平的男子往往要强些;我也以为男子们不妨对有学识的妇女开点适当的普通玩笑,有些人连讲点这样的笑话都十分害怕,以致对女友们绝口不敢谈论各种书籍学识,这实在是无谓的恐慌。其实,对这类戏谑的担优,只是在应付无知的妇女时才有意义,她们不配谈论知识问题,对于她们,男子们是避而不谈这类知识的。而这种情形也会使某些徒有虚名的男子装出一副比妇女优越的样子来。不过我想我的公正的读者们会确信,一切有健全理智的熟谙世事的人,对于他们知识范围内的这类著作都能作出种种不同的评判.并且比那些卖弄学问的愚钝作者和评论者更相信自己的优雅的鉴赏能力;尽管他们的鉴赏力缺乏规范的指导。在我们邻近的那个国家里①,良好的鉴赏力和风流豪爽同样著称,那里的女士们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学术界的权威,正如她们在交际界那样;要是没有她们的赞扬和卓越的评判,任何文艺作家都休想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她们的评判确实有时也叫人感到头痛,例如我发现那些欣赏高乃依②的贵妇们,为了抬高这位大诗人的荣誉,当拉辛③开始超过他时也要说他比拉辛更好。她们总是这样说:“真没想到,人都这么老了,还要同一个这样年轻的人作对,争什么高低,计较什么评价。”但是这种看法后来被发现是不公正的,因为下一代似乎承认了这样的判决:拉辛虽然死了,仍然是优雅女性们最宠爱的作家,这同男子们给予的最好评判是一致的。
只是在一个主题上,我不那么信任妇女们的评判,这就是有关风流艳事和献身信仰的作品应当如何评价的问题。对于这类事情,女士们通常感情过于激动,她们大多数人似乎更喜欢热烈的情感而不能保持适度。我把风流艳事同为信仰献身的事情并提,是因为实际上她们对待这两者感情激动的方式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感情有同样的气质作为依据。由于优雅的女性都富于温柔和热情的秉性,这类情景就会影响她们的判断力,即使作品的描述并不得体,情感并不自然,她们也很容易受到感动。所以她们不欣赏艾迪生关于宗教所写的优美的对话而喜欢那些讲神秘信仰的书籍;由于德莱顿先生④的挑剔,她们拒绝了奥特维⑤的悲剧。
倘若女士们的鉴赏力在这一方面有所矫正,她们就会稍微习惯于鉴赏各种类型的书籍,并能给有健全理智和知识的人们以鼓励,促进他们之间的交际,诚心诚意地协调一致,为我所提倡的学者和社交界的联合而尽力。否则,尽管她们也许能从随声附和者那里得到许多谦和的顺从,但学者们是不会随和她们的,她们也不能合理地期待诚实的反应。我希望,她们不至于作出那么错误的选择,以致为了假象而牺牲实质的东西。
休谟:谈谈写作的质朴和修饰
艾迪生先生认为,好作品是感情的自然表现,但不要明白显露。我觉得这还不能算是对好作品比较正确扼要的界说。
情感如果仅仅是自然的,就不能给心灵以愉快的感受,似乎不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水手的俏皮话,农民的见闻,搬运工人和马车夫的下流话,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也是挺讨人厌的。从茶馆闲聊里编造出来的无聊的喜剧场面,有哪个能忠实和充分地描写出事实和情感来呢?只是在我们把自然的种种美好和魅力描绘出来时,换言之,自然只是在艺术给予修饰和使之完美,不是简单地加以模仿而是按照它的应有的美的样子加以表现时,才能使有鉴赏力的人们感到愉快;如果我们描写比较低级的生活,手法笔触就必须是强有力的和值得引起注意的,必须能使心灵得到一个生动的形象。桑丘?潘沙①荒唐可笑的na?veté②(天真)在塞万提斯笔下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真是无与伦比,包含着多少豁达大度的英雄形象和温柔的爱情画面啊!
这一点对于演说家、哲学家、批评家,以及任何一个用自己名义写作而不是借助于他人的言语行为的作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他语言不文雅,观察力不出众,理解力、感受力不强,没有气概,那么他夸耀自己作品的自然和质朴就是徒劳无益的。他也许说得正确,但决不会使人喜欢。这类作家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根本得不到人家的指摘与苛评。幸运的书和人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冷遇。贺拉斯谈到过所谓“欺骗性的生活道路”,这条秘密的、骗人的生活道路,也许是一个人所能有的最大幸运;不过另一个人要是落人这条路,得到的却是最大的不幸。
另一方面,作品如果只是使人惊奇,但不自然,就决不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持久的享受。描写古怪的事物,当然不是模写或模仿自然。失去了正当的表象,画面就没有同原来面貌相似的东西,我们的心灵对此是不会满意的。在书信体或哲理性的著作里,过分的文饰是不适当的,史诗或悲剧亦复如此。华丽的词藻和修饰太多,对于一切作品来说都是一大缺陷。非凡的描写,有力的机智火花,明快的比喻和警句,如果使用得过于频繁,就成了瑕疵,而不再是对文章的润色了。这就像我们观看一座哥特式建筑时被花样繁多的装饰搞得眼花缭乱那样,由于注意力被各种枝枝节节的东西吸引而分散,就看不到整体了;心也同眼睛一样,它在仔细读一部堆满机智的作品时,也会被不停的闪光和惊奇搞得筋疲力尽,感到厌倦。一个作家要是才智过于丰富,往往就会出现上述情形;虽说这种才智本身还是好的、使人愉快的。这类作家通常的毛病,是他们不管作品主题是否需要,就把他们喜爱的修饰之词和手法大加卖弄堆砌;因此他们要表达一个真正优美的思想,就得用二十个矫揉造作使人厌烦的奇思怪想。
不过我在这里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那些把质朴和文饰恰当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尽管它们可能比上述那类作品写得更长更丰富。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我不想谈论过多,也要作少许一般的观察。
首先,我观察到:尽管两类过分都应当避免,尽管在一切写作里应当苦心探讨一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适当的中间方式,但持中的写法并不只限于某一种,它容许有很大的自由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想蒲柏和卢克莱修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大。在极端的精雅文饰和极端的单纯质朴两者之间,诗人似乎可以随心优游,不必担心会犯什么过头的毛病。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地带里,布满了彼此各异的诗人,各有特殊风格和面貌,这并不影响他们得到同等的赞美。高乃依和康格里夫①的机智和文采,在某种意义上比蒲柏还要强(如果各种类型的诗人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而索福克利斯和泰伦提乌斯比卢克莱修还要质朴自然,他们似乎超出了大多数完美作品所具有的持中状态,在这两种对立的特征上有些过分。照我的看法,在一切伟大诗人当中,维吉尔和拉辛处于最接近于中心的位置,离两种片面或极端最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观察到的第二点是:想用词句来说明质朴和文饰这两者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待中状态是什么,或者想找到某种能使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划清优美与缺陷的规则,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事。一个文艺评论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发表很得体的看法,但是它却不仅不能使读者搞清楚这些持中的标准或界限,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东西。丰特奈尔的《论牧歌》,是文艺评论中难以比拟的精品。在这篇文章里,他进行了许多思考和哲理的讨论,力图确定适合于这类作品的恰到好处的中和之道。可是任何一个读到这位作家自己写的牧歌的人,都会认为这位有见识的评论家尽管道理讲得好,鉴赏力却不佳。他所认为的完美,实际上过于强调了优雅文饰的方面,而这对牧歌是不相宜的。他所描写的牧人情感比较适合巴黎的妆饰,而不适于阿卡狄亚的山林;可是这一点你从他的批评理论中是绝对发现不出来的。他指责所有过分的描绘和修饰,所说的道理同维吉尔实际上做到的程度一样,仿佛这位伟大诗人也写过有关这类体裁的诗歌的论文似的。不管人们在鉴赏力方面多么不同,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见解通常是一样的。文艺批评如果不涉及特殊,不充分讨论各种例证,那是没有什么教益的。一般说来,人们承认美同美德一样,总是执其两端适得其中的东西,可是这个居中的东西究竟在两端之中的什么地方,分寸如何掌握,却是一个大问题,它决不能靠一般的讲道理得到充分的说明。
现在我来讲讲在这个问题上观察得来的第三点看法,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避免过分的文饰甚于避免过分的质朴,因为过分文饰比过于质朴更损害美,也更危险些。
这是一条确实的规律:机智与情感是完全对立的。去掉了感情,就没有想像力的地位。人心很自然地受到制约,它的各种能力不可能同时都起作用,某种能力越占上风,留下来供其他能力得到发挥的余地就越少。因此,描写人物、行为和情感的一切作品,比那些由思考和观察构成的作品需要有较大程度的单纯质朴性。由于前一类作品更动人、更美,按照上述见解,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在单纯质朴与文采修饰两端之间优先强调前一方面。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我们最常读的、一切有鉴赏力的人时时放在心上的作品,都有使人喜欢的质朴,除了附丽于这种质朴感情之上的优美表现.力与和谐的辞章而外,它们并没有什么使我们在思想上感到惊奇意外的东西。如果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讲出了某种机智的警句,它一上来就会打动我们,不过这样我们的心就要期待在进一步细读中了解这个思想,也就不再为它所感动了。我在读马提雅尔①的一首警句诗时,它的第一行就使我想到了全诗会说些什么,我不想重复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也就没兴致读这首诗了。但是卡图卢斯②的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价值,我在仔细读他的诗时从来没有感到疲倦。考利③的作品翻一下也就够了,可是帕内尔④的诗读到第十五遍,还同初读时一样感到新鲜动人二此外,作品和女人一样,某种平易的姿态和衣着,总是比刺人眼目的涂脂抹粉、装模作样、穿金戴银要动人得多。后者只能迷惑人的眼睛,却打动不了感情。泰伦提乌斯有一种最平和羞怯的美,他写的一切都使我们喜欢,因为他毫不虚假,他的纯净自然给我们以一种虽不强烈却是持久的感受。
但是,由于文采修饰多多少少也能算作某种美的东西,所以走这种极端是比较危险的,也是我们最容易陷人的毛病。单纯质朴如果没有同时伴以高度优雅和适当的风度,往往被看作平淡乏味。与之相反,机智和骗人的闪光就成了使人惊奇的东西。普通的读者受到它的强烈刺激,会错误地以为这就是最不简单的、最了不起的创作方法。昆体良说,塞内卡的雄辩里充满了使人喜欢的错谬,所以就更加危险,更容易败坏年青人和无知的人的鉴别力。
我要再多说两句的是,在今天,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加提防过分的文饰,因为学术有了进步,在各种类型作品的领域里都出现了有名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容易陷于这种极端。想靠新奇来取悦于人的努力,使人们远离质朴自然的感情,他们笔下就充满了矫揉造作和骗人的东西。古希腊小亚细亚的雄辩,到阿提卡就大大败坏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鉴赏力和天才,到了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时代就江河日下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类似的。何况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类似的鉴赏力下降的征候,法国如此,英国也是一样。
这两篇文章都是杨适先生翻译,出自休谟经典文存。让我们再来一篇奥威尔的。
奥威尔:政治与英语语言
小结
好文风是休谟、毛姆、奥威尔走的路线;是在The Elements of Style、 The Economist Style Guide中一脉相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