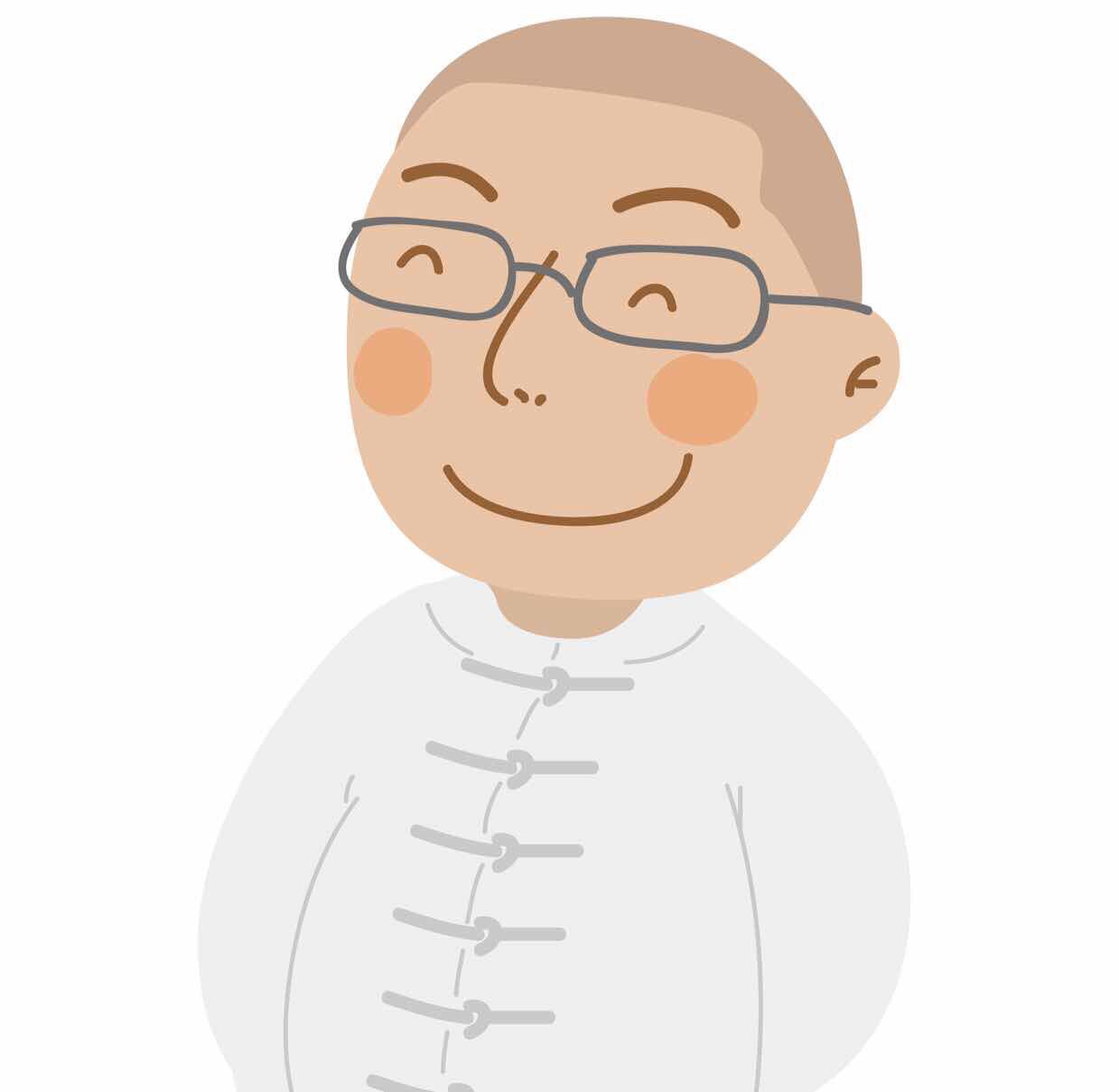舞!舞!舞!
我一直欣赏日本文学的细腻。当这种特质夸大为私小说浆糊后,多少令人不快。幸好村上不是。那份不同于卡夫卡的明朗与同样对工业时代人性的观照,都令我赞赏不已。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也许最有同感的是村上对于“迷失的自我”的寻找。
“寻找”始终是村上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无论是《挪威的森林》中的渡边还是《舞!舞!舞!》中的“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质问自己:“我在哪里?我是谁?”。在《挪威的森林》最后,绿子问主人公渡边他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顾电话亭四周。 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男男女女。 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连连呼唤绿子。
在这里,迷乱的地理位置显示渡边迷乱的内心,失去了精神寄托所在的直子无法回返往昔岁月,而现在的自己又将去哪里呢?又要抵达何处呢?或许只有当我们也失去了代表着过去的人、物,我们才能体味到这种站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空落。
村上的《且听风聆》、《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四部曲”中的“我”,亦有这种寻找的失落。寻找一只带斑点的羊,寻找始终未出场的喜喜,这类寻找其实不都是象征着寻找那些迷失的自我吗?略有不同的是,四部曲中的“我”从一出场,就是一类有点怪、空虚无聊的都市人,没有什么值得追忆的。于是小说从一起笔就洋溢着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感。《舞!舞!舞!》开篇写道:
这里是哪里?无须问,答案早已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人生。 若干事项、事物和状况。其实我并未予以认可,然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与我相安共处。 旁边有时躺着一个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自己并未栖身于任何场所。
即使已经拥有世俗的家园,但是使我们成之为人的精神该栖身何处?村上问道。为此,他不惜让在路上的主人公走向潜意识,如《末世异境》中在冷酷异境中生存的我;或者让主人公走向梦境或虚幻世界,如四部曲的我,《奇鸟怪状录》中的我,他们的最终走向可谓都是“虚幻”。
虚幻总归是虚幻,寻找到的最终结果即使为虚幻,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于是寻找便成为了无尽头,聊以自慰的最终目的。一位又一位“我”便在不断地寻找,不断地体验空虚。“不要去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人们只是不停地舞!舞!舞!.
当整个都市以比特节奏在Internet上狂舞着,村上笔下的寻找者们在21世纪则成了“浏览!浏览!浏览!”。由一个链接转向另一个链接,却不知可以让心灵停驻的港湾在何处。于是现代人便如同穿上红舞鞋一样,永不停歇地狂舞着,旋转着——直到世界终日。但是到了那里,我们又能找到迷失的自我吗?《末世异境》中的篇末,我在失去自已的影子之后感道:
觉是自己好像一个人被遗留在宇宙的边上一样。 我已经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回了。 这里就是世界的终点,世界的终点不通往任何地方。
上帝说,孩子,跟我走吧,你将幸福!但是亚当和夏娃还是偷吃伊甸园中的智果,于是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感到羞耻,因为自己是光腚的。孤独与恐惧相随自由而生。这似乎意味着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随着人类自由的增加,我们反而会觉得日益孤独。
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是极度自由的,拥有寻找的权力,诉求情感的可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只会感到孤独呢?为寻找而去寻找,为了获得自我而让自我迷失。只能选择舞!舞!舞!的存在方式呢?如《舞!舞!舞!》中的五反田对疯狂运转的日本相当不满,进而不满意作为电影明星的自己,力图直率地生存下去最终却还是无法找回自我,杀死高级妓女咪咪和喜喜,自己亦投海自杀,企图获得自我的结果竟是进一步迷失自我!
这种悖论多么像弗罗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现象。现代工业社会在让人进一步掌握大自然的同时,也发展了孤独感空虚感自卑感。就像亚当夏娃揭示的人类生存悖论一样。人可以自由地面对他人,但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却同时而来的是与自然的断绝,经常要直面尖锐的利益冲突。
为了避免孤独,人们索性逃避自由,放弃个性,回归群体如法西斯主义,如集权政府,从而获取安全感。在《奇鸟怪状录》中的“我”下到井底,苦思三天三夜的片段尤其富有象征意味。我可以自由地聆听与诉说,却放弃交谈,走不出心中的井现实的井而仅仅是将自己自闭于井底。
在村上笔下,主人公们就是这么一群很真实很空虚的小人物,被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掩蔽着自我,既然不想依靠政治与技术筑成的都市巨壳,那么当然很难真正摆脱无意义感,于是只好不停地舞!舞!舞!
有一首流行一时的歌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这里,我们将故园假设为在远方,在缥缈的远方。为什么不如村上春树般坦言:“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将寻找”呢?纵然寻找的最终结果只说明自我存在的唯一意义在于:舞!舞!舞!